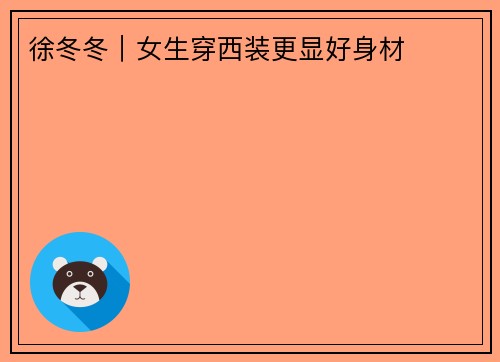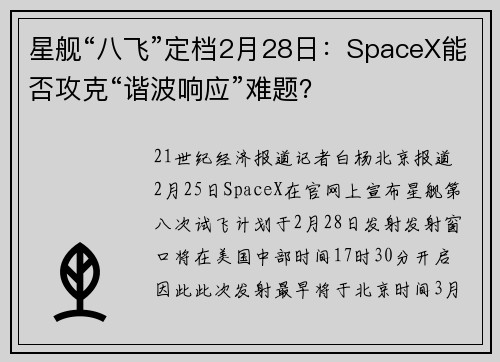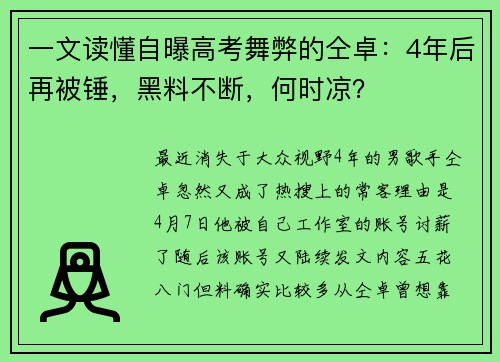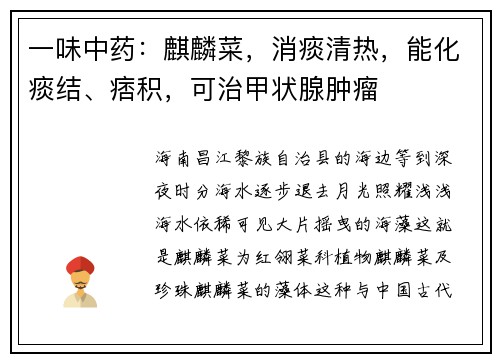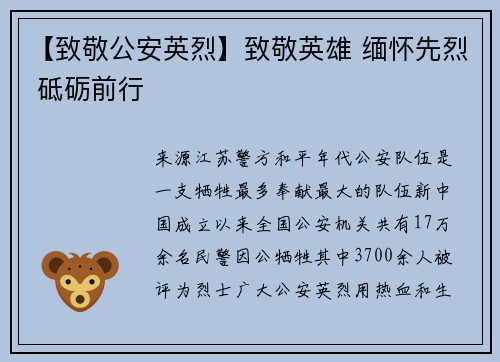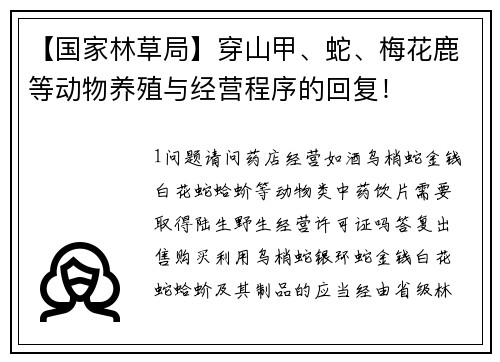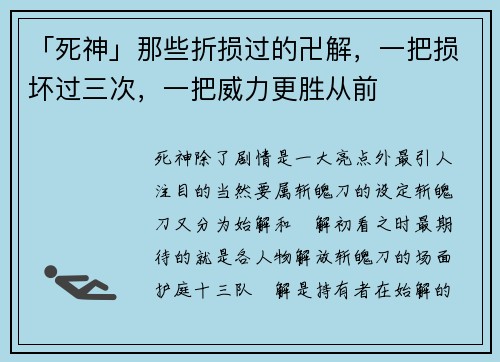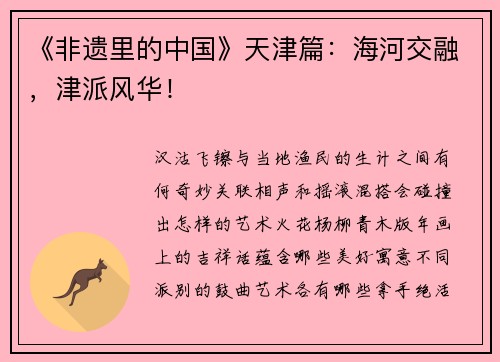我是“亚细亚”

金州纺织厂的纺纱车间
我相信金州人都知道“亚细亚”这个名字。我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讲过“亚细亚”的故事,亚细亚原本是一种特快列车的称呼,而这个“亚细亚”,却是金州纺织厂的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,她也不知怎样给人叫成了这样一个挺奇怪的绰号。
“亚细亚”的故事挺传奇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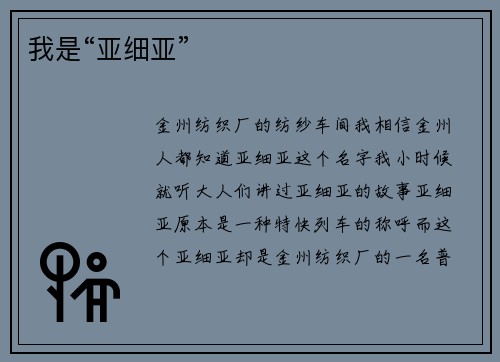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一个身上穿着旧工作服的中年女人走进了大连秋林商店,她走到了手表专柜,让售货员把那块四百六十多元钱的欧米茄手表拿出来瞧瞧。售货员根本不相信这个女人能买得起这样世界名表,可人家偏偏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把钱时……售货员傻眼了,她一边应付着这个买表人,一边暗暗地通知了商店的保卫科。保卫科的人来到了柜台,问这个买表人,你叫什么名字?那个女工答道,阎凤云(记忆中她叫阎凤云,时间太久,可能有差错,希望金纺老工人们更正)。
保卫科的人再问,你在哪个单位工作。那个女人答道,金纺。金纺就是赫赫有名的金州纺织厂,保卫科的人拿起电话,直接打到了金纺保卫科,问,有没有阎凤云这么个人?她能买得起四百六十多块钱的手表吗?保卫科回复,没有这么个人……这时候,站在一边的“亚细亚”把电话抢了过来,大声地喊道,我是亚细亚。电话那头的人赶快说,对对对,我们厂有这么个职工,别说一块手表,就是十块二十块她也买得起。
好多年了,金州大人小孩子没有不知道金纺有个“亚细亚”。关于“亚细亚”的传说有很多,有说她是因为干活快,操作利索,如同当年跑在大连到哈尔滨铁道上奔驰的一趟特快列车,列车名称为“亚细亚”。也有说,“亚细亚”曾经有过一个未婚的男人,男人离她而去时,乘坐的就是“亚细亚”列车,不上班时,她经常到火车站去等这趟亚细亚快车。不管怎么说,“亚细亚”所以传奇,还是因为她人过中年,一直单身,是个老处女,而且特别能干活,是个操作能手。
亚细亚能干,干起来飞快。不仅她一个人是这样,那一代人也都这样。有一位当年的劳动模范,大家让他谈谈体会,为什么这么干?劳动模范说,“小鼻子”(日本人)在时,俺们就这么干。后来,这成了一句笑谈。其实,抛开意识形态,通过这个笑谈,就能看出当年工人们的工作态度。
记得那是一九八四年,“亚细亚”已经退休多年了。有一天,金纺的老作者周莹老师找我,问我想不想写一写“亚细亚”?
因为心中的“亚细亚”一直是个谜,我当然想写一写这个挺神秘的纺织女工。一天下午,周莹带着我去了金纺的职工宿舍,在一间宿舍里,我见到了这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人物,“亚细亚”。看得出来,她是一个不太愿意让人走近她的女性,她已经六十多岁了,仍然留着长长的自然卷发。她的面庞消瘦,显得鼻子高高的,她那双大眼睛,如同一湾清澈的水,很单纯,很透明。
安博电竞·(anbo)官方网站周莹跟“亚细亚”介绍了我,还有一个女工模样的人,说是亚细亚的妹妹,凑近她的耳边,说话声音很大。因为我在棉织厂工作过,我知道,因为机器的噪音,许多纺织工人的听力已经减弱。我让“亚细亚”随意讲,讲述自己的过去,讲一些她的经历。
“亚细亚”不太善谈,她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,她家在乡下,她十三岁那年,就来到了内外棉(金纺日伪时期的名称)她的手头快,领会能力也强,培训没有几天,她便能上岗操作。“亚细亚”当年的一位工友跟我介绍,那时候,日本人一色招收十三四岁的女孩子,进到内外棉的女孩,都是穷苦人家的姑娘,因为贫穷,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工作为家里挣钱,穷人家的姑娘都不能放弃。
解放前,金州内外棉(日伪时期的工厂名称)的生产车间
“亚细亚”很快在这群姑娘们当中展露头角,她当了一个类似班组长那样的角色。在纺织厂工作,付出的不仅是汗水,有时候,还要受到工头和坏监工的欺辱。有时候停电,借着这个机会,一些工头和坏男人便欺女孩子。每到这时候,“亚细亚”便会钻进机器下面躲藏起来,让坏男人找不到她。后来,她渐渐地长大了。再遇到停电,她也不再躲藏,而是手中握着一支织布梭子,梭子两头都是尖尖的铁头,有坏人打她的主意,她就狠狠地用梭子打他们。坏男人也领教了“亚细亚”的厉害,没有人敢欺负她。
“亚细亚”最让人敬佩的,就是她的工作精神,从进到工厂那天起,她就一直努力工作。刚刚光复时,很多人都不上班了,可她还是坚持天天上班。那年冬天,天降大雪,路面上很滑,亚细亚摔倒在地上,摔折了小腿。让人想不到的是,她竟然爬进了工厂,用木板和绳子,将骨折的小腿捆扎了起来,照样上岗操作。她的手指也曾经骨折过,可她也是一天不休息,用绷带包扎起来。
记得采访“亚细亚”那天,她伸出手来,让我看她那已经变形的手指。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敬重的生产能手,在文革期间也受到了触动。触动的原因,就是她曾经在解放前,当过类似一个小工长那样的职务。
解放以后,“亚细亚”真的成了亚细亚了,因为性格的原因,因为她不会说道,人人都敬佩“亚细亚”能干,真正的生产标兵,却不是真正的劳动模范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,因为有奖金制度,不是劳动模范的亚细亚,却总是能拿到最高的奖金,她的工资不菲,加上奖金,她一个人生活,什么负担也没有,她对自己十分苛刻,到食堂里吃饭,吃的也是最差的伙食,有时候,只吃一点咸菜。“亚细亚”从不打扮自己,一年到头,身上穿的就是工作服。除了工作,“亚细亚”剩下的就是攒钱了。人们经常在背后替“亚细亚”算账,五十年代那会儿,她已经成了万元户。
在人人吃大锅饭的那个年代,“亚细亚”确实有不少的积蓄。但她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吝啬,她经常会拿出钱来,帮助自己身边那些有困难的人。
金纺二织布,最大的织布车间
“亚细亚”是八十年代初期退休的。退休的第二天,她照常上班。车间主任也拿她没有办法,她就是要工作,什么工作都可以。车间主任只好让她去操作那两台小型织带机,专门织包装棉纱和棉布用的小背带。
从此,“亚细亚”天天风雨不误,天天上班织小背带。织带机器坏了,她便去废铁堆里找配件,多少年的工作经验,她也学会了修理织机。退休以后,她摸不到真正的织布机,便从小两台小织带机上继续着她的工作梦想。年复一年,终于有一天,小织带机再也开动不起来了,工友们劝她,回家吧,好好休息吧,干了一辈子啦,也该休息休息了。
家?她有家吗?“亚细亚”已经把金纺当成了她的家。她住在单身职工宿舍里,她一辈子单身,退休以后,她哪里有家啊。她把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台机器,她的命运已经与金纺的命运联在了一起。她把她的热情,她的全所生活都寄托在了机器上。“亚细亚”的人生结局我并不知晓,但我祝愿,她最好不要看到自己寄托全部生命的金纺不景气甚至倒闭。带着灰心和丧气甚至绝望去了天国,那样她会更加抑郁。如果“亚细亚”谢世时,金纺的纺纱机织布机仍然轰隆隆地运转着,工人们一天三班倒,即使她去了天国,她仍然会在织布机中间走巡回,一个挡车工一个班次的巡回走下来,整整六十华里,这是有人测算过的。“亚细亚”只是纺织女工们当中的一位,多么优秀的产业工人,在现实当中,她们不再走巡回,而是从希望走向了无望,甚至绝望。
金纺的纺纱车间
后来,周莹又找了达理夫妇来写“亚细亚”,后面的事情,我就知道得不多了。为什么想起了“亚细亚”,还是因为回到故乡那天,车子正好路过金纺。如今这个东北最大的纺织厂,已经名存实亡了,不是当下才停产倒闭,而是早已在很多年前,金纺就走到了尽头。工人买断工龄,下岗回家。工厂的决策者们决定把厂房和地皮卖给开发商,遭到了工人们的反对。
我想,决策者一定对金纺这个工厂,对工厂里的工人们一点感情也没有。要知道,当时的金纺有两万多名职工,金州小城才有几万人哪,一个金纺似乎牵动着千家万户。时间流逝,记忆正在淡忘。如果我不回到故乡,我也不会想起金纺,不会想起“亚细亚”来。那一代的中国产业工人,应该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产业工人。多好的工厂,多好的工人……
让我说什么好,那些把金纺干黄了的人,他们内心深处不愧疚吗?